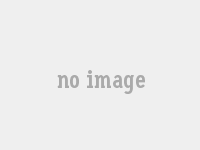很少有人称他们为“英雄”,但他们总是伴随事故、灾难和不幸一起登场。山地走失,意外落水,高楼火警,极端天灾。在后续的警情通报或新闻通稿中,他们的称呼常常与当事人并列出现。好消息:获救。坏消息:找到。这两个动作共同的终点,总是他们。
信息洪流中,“救援队”三个字往往只是一瞥而过的背景。在以秒争夺注意力的舆论场里,就连它最重要的前缀——“民间”,也常被省略。
民间救援队:以提供应急救援为主要服务内容的社会组织。
——搜索引擎如此定义。几十个字的冰冷释义背后,一种基于自我奉献的“反人性”逻辑,以及持续的群体性付出,正在静默运行。
这究竟是一群怎样的人?身为局外人,找到答案的唯一方法,是去看一看他们眼中的世界。
山中来电
饭桌上,电话铃声响起。“110来电。”救援队队长张玉忠说着接起了电话。三三两两的闲聊戛然而止,所有人的注意力转移到了这部正在通话的手机上。
有人在崂山上迷路,需要救援。
“电话多少?”张玉忠问电话那头的接警员。一个眼神信号发出来,站在一旁的队员默契地掏出手机开始记号码。
“我找不到下山的路了。”电话拨过去,一个年轻男性的声音,“我不知道在哪个位置,也不知道从哪里上的山。”一句话让现场炸开了锅,大家七嘴八舌开始出主意。
“问他眼前能看见什么。”
“从太和位置上的山吧?”
“外地人不熟悉路,你说这个他不知道。”
张玉忠一把接过电话。“你手机还有电吧?你加我微信,先发个位置。”
这天是11月的一个星期六,这支民间救援队例行组织实训演练。照例,队里大部分核心骨干队员到场参与。
正是午饭时间,大家从四处的训练点聚拢到这个还在施工的新的训练基地。菜是几个队员在院子里用大锅炒的,凳子是东拼西凑现找来的。被电话铃声打断时,他们开饭不过半个小时。
看到报警人发来的一条实拍视频,一个队员脱口而出报出了具体位置。他叫马小明,是山地救援组的总负责人,队里各项救援技能的培训指导员,也是队友公认的全能型体能王者。“整个青岛的山,他走遍了。”提起马小明时,几乎每位队员都会加上这一句。凭借有限的信息迅速锁定山地走失者的位置,是他最著名的技能点——当然,范围在青岛市辖区内。
这个46岁,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至少年轻10岁,外形精干,戴着500度的近视镜,上牙掉了一颗的先锋队员,脸上永远挂着温和的微笑。众人讨论时,他提议,“去两个人把他(迷路者)带下山”。
“这个事不急。”张玉忠开口说,“你们先好好研究。”报警人位置明确,手机有电,正午当头,距离天黑尚早,警情算不上危急。他一条条分析给队员听,然后给出建议:先通过微信语音引导迷路者自己走下山。
一旁的队员开始尝试语音远程指路。“信息不要太乱,慢慢说明白。”张玉忠坐下来,一边大口嚼着馒头,一边叮嘱。
见语音发了一条又一条,对方仍摸不清方向,两位心急的年轻队员决定开车前往警情现场——地图显示,在30公里外。话说着,人就冲了出去。其他人自然过渡到下一个环节:整理装备,前往下午的训练场地。至此,午餐结束了。
“他很急。”在上山准备绳索训练的路上,张玉忠对我说,“一般情况下,这样的救援我就提前筛选了,能语音引导的,就不派人去了。这个过程是一步步来的,他还属于莽撞人一开始的状态。”
他口中的“莽撞人”,正是刚才冲出去开车前往救援现场的那位队员——态度积极,能力不错,入队不过一年。
他当然也记得,在成为如今带领826人队伍的救援队队长之前,在拥有当下这份沉稳的判断力之前,他自己也曾是“莽撞人”。那是18年前的事了。
马小明正在进行山地绳索训练。
绳索训练项目的准备工作十分繁琐。在生命健康面前,每一种小心谨慎都不为过。
莽撞人阶段
对外讲起救援队的发展历程,张玉忠习惯从2008年开始算起。那一年被称为“中国应急志愿服务元年”,两件前所未有的大事在中国大地相继发生:汶川地震——约300万国内外志愿者深入灾区,北京奥运会——约170万志愿者参与服务。
张玉忠既不属于300万分之一,也不属于170万分之一。但这些事件间接地与他有关。
他是青岛城阳区人,1972年出生,初中毕业后开始学习修车,20岁开始经营自己的汽修厂。因修车,他开始频繁接触事故车辆。那些惨烈的事故现场没能吓退他,关于救援的使命感,却于彼时萌芽。“你看人的生命,很脆弱,一旦发生灾难、事故之后,就没有了……”
渐渐地,协助相关部门共同处理交通事故现场成为他的工作常态。“听到120、122有什么(事故现场),我们就去参加。”也是在那个时期,他的汽修厂迎来搬迁,新场地尚未确定的空隙,他拥有了一段时间的闲暇。原本就对户外活动感兴趣,他将大量时间投入登山和钓鱼,长时间泡在户外,遇到山中走丢的人,意外落水的人,他自然而然前去帮忙。一批志同道合者在那时相遇。
多年后回想起来,他意识到,“那就是救援队的初始阶段”。
时间线拨回2008年,汶川地震的新闻撕裂日常。民间力量自发赶赴灾区的电视画面让他们坐不住了。几人迅速碰头,决定立刻行动。物资尚未齐备,次日官方的公告却为这份热忱划定了边界——“不提倡社会人士参与救援”。亲赴灾区的计划没能成行,他不死心,开始多方搜寻信息,一探究竟。
关注得越多,受到的冲击越大——民间自救发挥了巨大作用是事实,但一些无序、非专业的救援力量在救援行动中产生的阻碍也是事实。由此,他得到一个新的启发:“救援不是靠一腔热血的,需要组建队伍。”
这份个体的意识觉醒与时代趋势几乎同步。那一年,在经历巨大灾难的考验和国际盛会的锤炼后,全社会的志愿力量被激发、被看见,更重要的是,志愿团队在服务过程中暴露出来的“热情有余、专业不足”等问题也直接推动了政府着手构建应急志愿服务的国家体系。
中国的社会志愿服务力量正在被重塑。汇入历史洪流,张玉忠的救援队成立了。那时,城阳区发布了一首名为《一城阳光》的歌,北京那支著名的救援队名叫“蓝天”,他索性取了“阳光”二字为自己的救援队命名。
那是一个新的开始。他们有了名字,有了颇具凝聚力的初始队员,有了纪律,有了一个明确的目标。但要组建一支专业救援队,这些远远不够。
正规化以后,救援行动不再局限于户外活动时的“顺便为之”。 QQ群建立起来了,各种各样的求救信息弹出来,队员们开始奔赴各种各样的现场。他们很快发现,会修车、游泳、能在山里找到人,这些民用技能与专业救援之间,隔着一道需要系统训练才能跨越的鸿沟。
“一次次出的出的现场不一样,在这个过程中,你就知道哪个技能重要了。”山地救援需要用到绳索技术,水上救援要会操作冲锋舟,碰上复杂的状况,还要会潜水,火灾现场也要去,队里还缺一辆小型消防车……就这样,他们边救援,边学习,边买设备,一年又一年,队伍在实战中走向专业和成熟。
回想那些日子,一些画面浮现出来。听说山上有人走丢或受伤,他曾不管不顾开车冲出去,路遇红灯,“闯就完了”。那是张玉忠的“莽撞人阶段”。“现在再去做这样的事情,不可能了。”53岁的张玉忠像是在与18年前的自己对话,“首先你得遵守交通规则,连眼前的规则都遵守不了,你怎么样去救别人?”
冲锋舟。
来者不拒
李皓是在五六年前加入救援队的。他年过五旬,但身形利落,不见丝毫臃肿和老态,肤色白净,说话时露出酒窝。初见面时,他身着正装,见到陌生人,热情而健谈,身上散发着友善。
那天是一个星期四,恰逢救援队每周例会,结束本职工作后,核心骨干们陆续前来,张玉忠迅速挨个介绍了在场的每个人,轮到李皓,他特别强调:他年轻时曾在部队里开战斗机,“能力很强,不管是无人机,潜水,搜救犬,山地救援,他全部都能”。
爱好广泛,是李皓的显著特点之一。他擅长多项户外运动,是资深马拉松、山地越野赛跑者。由于跟随的跑团和阳光救援队合作密切——救援队为跑团提供赛事保障,跑团成员因体能及对山地熟悉等优势,也常常支援救援队的山地搜救行动——一来二去,李皓就这样成为救援队的一员。毫无意外,跑团团长也在救援队里。
入队后,由于能力突出,他很快晋升为副队长。绳索,无人机,训练搜救犬,无线电,以及潜水,都是入队后学的。
翻看李皓的朋友圈,你会为他超出常人的热情、精力和学习能力赞叹。他养着一只猫,对大型绿植也颇有研究。他动手能力极强,疫情期间家里装修房子,工人难找,他自己上手贴了瓷砖。这些年来,除了跑团和救援队,他在多个社会公益组织中活跃,2024年,他拿到了青岛市无偿献血荣誉卡——累计献血量超过4000cc的市民才可以获得。山水,美食,运动,公益,他的生活热气腾腾。
“业务聚人气。”聊到大家加入救援队的原因时,李皓说。这里说的“业务”,即爱好。在入队前,拥有一种或多种爱好,是大多数队员的共同点。
秘书长刘广耀生于1976年,是一名无线电爱好者。2009年的一天,他偶然在附近搜索到了一个叫作“阳光救援队”的无线电频道,通过短波语言,双方建立了联系……等等,救援队为什么会有无线电频道?如果你提出这样一个外行的问题,队员们会反复给你讲述一个故事:汶川地震后通讯完全中断,是一位叫作刘虎的无线电爱好者用短波从震区发出了第一个求救信号。
如今,队里的核心成员几乎人人都考取了业余无线电操作证。外出训练时,他们习惯用对讲机而非手机交流,呼叫对方时用的是无线电代号而非名字。张玉忠的代号为BH4 IYR——这也是他的微信昵称。一个人的爱好变成了一群人的。
若作为局外人潜入他们的通信频道,会有置身无线电谍战剧的恍惚:对讲机噼啪作响,夹杂英文代码的行话经电流过滤,形同加密通讯。当然,这里的“加密信息”也很接地气,你会在一些严肃的坐标回报中听到一句:“你们一会谁回来的时候买点馒头。”
除了爱好者团体,还有一些队员是经亲友介绍来的。来自泰安的曹传海就是其中之一。从老乡那听说了救援队,他兴致勃勃加入,又苦于没有找到可以为救援事业贡献的一技之长。直到有一天,张玉忠去他经营的工厂参观,意外发现他养了很多犬。
“你喜欢养犬,那你就适合养搜救犬。”张玉忠马上指出。“原来救援队还可以养搜救犬?”曹传海喜出望外。那天之后,二人共同去北京住了7天,在国家地震训练基地学习了搜救犬训练的技能。很快,曹传海表现出对训犬事业的痴迷,他自费将搜救犬训练基地建在了自己的工厂里,并一次次扩建,也在救援队里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搜救犬中队队长。
还有一些队员的入队故事,仿佛一场命运安排的闭环。有一年夏天,一位经验丰富的登山爱好者在山中迷路报警。因求救者手机没电,夜晚又下起了雨,搜救难度大增,队里派出一波又一波队员进山搜寻。救援成功后,被救者为如此声势浩大的搜救行动感动不已,特意前去道谢。
“我说你也不用感谢,你就回来领着我们的队伍再去复盘,你当时究竟躲在哪了?”张玉忠说。后来,复盘会开了,再后来,这位被救者成为了救援队团岛站站长。
“来者不拒,只要你认可咱们理念,遵守咱们规定,随便来。”李皓总结。
秉持这样开放的纳新原则,救援队很快“卧虎藏龙”。如今,826人的队伍里有老木匠,电焊工,医生,心理咨询师,摄影师,资料整理员,后勤保障,全国女子铁人三项赛冠军,山地探险专家,资深飞控师,甚至,还有一位马术俱乐部主理人。
海上救援训练,图为三名队员正在进行冲锋舟训练项目。
消防演练现场。
怕出事,才不出事
即便到了今天,2023年北京门头沟与2024年郑州的洪水,仍是队员们聚在一起时会提及的案例。建队多年,老队员们历经救援无数,但大家公认的,震撼与无力感最为彻骨的还是这样的大型自然天灾。“范围太广,不是一个点,而是整个城市瘫了。”李皓说。
救援现场往往惨烈,但与普通人相比,救援人员视角里还有别的冲击:门头沟水灾,山洪迅猛,水流湍急,水中漂浮物太多等原因,导致一艘橡皮艇翻船,艇上人员均被急流冲走……救援世界不是成年人的过家家,这里伴随着牺牲、流血和隐秘的伤害。
郑州水灾时,张玉忠组织了130人的队伍去现场支援。疫情期间,救援队承担了入户消杀的工作,正是谈疫色变、人人自危的特殊时期,他们穿上防护服、背着消毒剂轮流进入“密接者”和“疑似感染者”家中、医院消毒。那段时期,所有参与人员住在救援队里。
这是一份伴随危险的工作,张玉忠给队里买了特殊的意外保险,整个团队共享60个名额,谁要出现场,提前一天将保险转移到其名下——这是近几年保险公司新推出的险种。“国家政策好。”他心怀感激。
幸运的是,这么多年来,队里出险频率不算高。最严重的一次事故还是几个月前,一次山地救援返程中,天色暗,路又滑,领队的马小明不慎摔倒受了伤。是的,他口中那颗少了的牙,就是那次意外的结果。
“当时没想到是断了,觉得这个牙怎么有点活动啊。”我问起这个故事,他有些难为情,轻描淡写地说。“下巴还缝了12针。”一旁的其他队员补充,“能力再强也有意外。”
细细追问,几乎每位队员都能讲出一个关于“危险”和“恐惧”的故事。
张玉忠记得,20年前最初接触交通事故现场时,面对血腥的场景也会不知所措。“第一次不敢伸手,第二次就慢慢搭把手,时间再久,就自然地接受这些东西了。”
“你干这个,必须到现场,你要救援嘛。”刘广耀说,“但很多时候也会害怕,再怎么说,人心是肉长的。”
李皓的“心惊”时刻总与溺水有关。他水性极佳,常参与水上救援与打捞,见过了太多溺亡者。一些画面记忆犹新。一次在白沙湾参与捞尸,钩子钩上来,他一眼看到一张年轻的脸。“哎呀,突然看到,好像心里就不得劲了。”他回忆。同行的新队员,因遭受了难以平复的心理创伤,此后的活动再也没有出席过。
有一年,队友们一起去一个大型水库搜寻一个溺水的小女孩。历经几日,各种工具用尽,还是没能找到,最后,一位队友潜入水中在石头缝里找到了女孩的尸体。“很多时候你会看到家属是真着急啊,特别是小孩的家属。”李皓说,“救活了很有成就感,但捞尸也是积德行善,至少给他们一个完整的归宿。”
见多了生死,他们的心没有更麻木,而是更敏感,更警惕。有一次安装师傅来家里装空调,李皓一下子注意到他们没有系好安全绳,于是严肃提醒对方要安全操作。“他说没事,我常年干。我说别没事,万一滑一下子。”
有队员开车经过跨海大桥时,总会习惯性观察,遇到疑似轻生的人,就立刻报警。以往经验和救援的使命感让他无法坐视不管。
控制风险的精神,与探索险境的冲动,在他们身上一体两面。聊到极限运动他们仍会两眼放光,仍梦想着去攀最险的峰,潜更深的海。如何理解这种悖论?“任何事情讲究科学,不是盲目冒险。”李皓解释,“首先你要怕死,怕出事,才不会出事。”
搜救犬中队副队长丁安来与他的伙伴“淘宝”。
苦的,甜的
采访的最后一站,是在张玉忠的家里。他在城郊租了一套一居室,和妻子带着两岁半的女儿同住。听我说想登门拜访,他有些不好意思:“房间很简陋。”在另一个对话场景中,他告诉我:“36个救援站点,都是我的家。”
这18年来,个人在救援队究竟投入了多少钱,他从没细算过,“你没法算”。 救援服务是免费的,队员也无偿奉献。可一旦走上专业化,装备就成了无底洞。如今队里拥有16辆车,包括3辆消防车,一辆宣讲车;每次外出培训、救援,所有人的差旅食宿都由队伍承担;遇到耗时长的任务,他还想给队员发些补贴。“一年花个百八十万不是问题。”
早年间开汽修厂,后来又做厂房出租,挣来的钱除了维持家用,稍有余裕都被他悉数投入到了救援队。几位核心老队员也各自出力出资。在漫长的初创期,这便是他们维系运转的全部根基。“有多少钱就干多大事业,没钱的时候也没办法,只能说看到好的装备,再等等,赚了钱再买呗。”他回忆。
转折发生在2015年。队伍开始承接政府的培训项目,有了相对稳定的课时收入。而早在2012年,各区陆续提供的免费驻地与仓库,也帮他们卸下了沉重的租金负担。从纯粹自我消耗,到逐渐获得外部“输血”,多年的努力在2020年给出了一个令人惊喜的答案:账面上,收支首次平衡。那是至今唯一一次,张玉中感受到如释重负的轻快。
救援事业做得风生水起,但张玉忠个人的经济状况却一直谈不上宽裕,生活上需要精打细算,女儿大多数的衣物,都是朋友家孩子穿小后传递过来的。另一方面,他似乎乐于这种清简。“小房子蛮温馨的。我觉得我吃得也很好,大家一起包饺子做饭,每天热热闹闹的。”他说,“现在感觉挺好的,也没有其他爱好了,救援就是我的爱好。”
他用洋溢着幸福和满足的神情讲述这一切,让人很难怀疑这些感受的真实性。
煎熬的日子早就过去了。那是2015年之前,前妻不满于他对救援队的过分热情投入,担心未来“家都败没了”。实际上,他早就上交了家中财政大权,救援之余的所有时间,也都投入在家务及厂房出租等事业上。“队伍大了之后,大家互相帮助,可能有更多机会,共同发展。”他极力解释,前妻不解。
他重感情,不是随意放弃家庭的狠心人,只是彼时队伍已建成,队友间建立深厚的情谊,又怎么能割舍得下呢?
他记得那一年,大家在红岛进行水上搜救,搜寻了两天没有结果,一支又一支救援队闻讯赶来,一大群人吃住睡都在现场,坚持了很多天。有一天,来自威海的一支救援队联系他:“你那边有没有声呐?你最好用声呐把周围仔细搜索一遍。”“没有。”对方立刻组织了3人,带着3台声呐当天赶到现场,没顾上吃晚饭,搜寻至次日凌晨两点。
“我们明天要回去上班了,你们会不会用声呐?”“不会。”于是,对方为他们彻夜培训。临走前,留下了3台声呐设备。
讲起这个故事,张玉忠流下泪来。“一次次的救援中,也被别人感动,看到别人干的事情,自己也就放不下了。”
2015年,他办理了离婚手续,净身出户。
那是一段艰难的记忆。失去了工厂、房子和积蓄,他身边只剩下一辆厢式货车。有任务时,它就是救援车;无任务时,他去莱阳队友家装满一车梨,拉到市场上卖;夜晚,他睡在车里。
“那个厢式货车,我觉得住得很舒服啊。”他说。对救援人而言,这不算什么苦。2012年底,在轰动岛城的“寻找崂山走失的老高”行动中,他带队在山上扎营。夜里气温降至零下16摄氏度,裹着两层睡袋仍冻得发抖,他们就这样硬扛了五天五夜。
“比起那时候已经很好了。”他说,“感觉无拘无束,很自在,甚至想到,反正家人生活都有保障了,假如哪天有特别的危险,自己也无所谓了,可以牺牲了。”
那辆厢式货车早已超期退役,如今仍停放在救援队停车场里,成为他忆苦思甜的载体。“每次到了特别难的时候,就想想那时候,看着它就提醒我,别乱花钱。”
队员们一起训练。从左到右依次为纪翠尚,马小明,刘广耀。
训练结束后,队员们合影。
信仰
在救援队里,他认识了现任妻子。他们一起救援,一起参与学习培训,慢慢走到了一起。“咱们干公益,也不适合结婚,要不然就搭伙儿过日子。”他曾这样建议。但妻子有自己的坚持。
婚后,妻子除了做自己的个体生意,照顾家庭,还兼任队里的培训讲师,很多时候,队友们出去救援,她在家里给大家做饭。
在张玉忠眼中,妻子不是追求名利的人,只是有时聊天中,她不经意“抱怨”一句:“咱们这一年搬好几次家哦。”张玉忠宽慰她:“树挪死,人挪活,我们越挪越活。”妻子笑了。
2023年,他们的女儿诞生,家里增添了新的欢乐,他相信这是自己做好事积的德。人生至此已是圆满。“人生不是你吃得好、住得好就舒服了,我觉得干着有意义的事,更舒服。”他说,“热爱就像信仰一样,你会为它不计代价。”
在张玉忠家里,我见到了他的父母。午饭时间,老两口做了一桌子菜等待客人到来。86岁的母亲听力不好,不明白记者的问题,于是自顾自开始讲述:
“玉忠从小就调皮,好打抱不平。见谁欺负弱者,他就去给人家报仇,最后反被一群人追着打。挨打了就受着,反正我替弱者报仇了。
不着家,干个救援队什么也不顾,吃不上饭了,没钱花了,就回来找爸爸妈妈:帮帮忙吧,孩子们要吃饭,有没有钱借我们用用。怎么能叫借?他也还不了,自己能吃上饭就不错了。
没有办法,为人民服务,无私奉献,就是这么个条件。反正你走正路,干好事,我们当你的后盾。”
老伴在一旁听着,起身去屋里,回来时拿着自己参加援越战争时的勋章和荣誉证书。他参军10年,退伍后回到社办企业做厂长,同时还是民兵团长。有60多年党龄,退休后,仍每天坚持看新闻频道和军事频道,这一生都笃信:为国家,为人民奉献,就是走正路。
两个儿子耳濡目染,从小向往当兵,但因客观条件,没能实现。二儿子张玉忠初中毕业后,突然对父亲说,不想上学了,想去开车。在当时的环境里,开车被认为是“很了不起的工作”。
父亲表现出极大的包容和支持。他说:“学开车也可以,但是不是应该先学会修车?”张玉忠一想有道理,就进了一家汽修厂做学徒。一同进厂的其他学徒都是被动去的,干活不积极,只有他发自内心爱上了修车,脏活累活抢着干,钻研起技术来,不分白天黑夜。同事都笑他,“这人傻乎乎的,下班不回家,自己花钱去学习”。
20岁那年,他在村里开了自己的汽修厂,因为修车技艺精湛,名声传到隔壁村,不少人专门跑来找他修车。他是优秀的技工,却不是聪明的商人。车修好了,他总不好意思收钱。因此,汽修厂看起来红火,几年下来,钱却没赚到。
他践行着一套独特的商业逻辑:多年来修车让利的“亏损”,或许是他最成功的“投资”。这笔投资在他盖厂房时兑现了——见他经济困难,正是这些老顾客们有料出料,有力出力,大家共同帮忙把厂房盖了起来。他第一次明白:原来善意是一场循环,最早受益的,可能是自己。
后面的故事我们都知道了。几年后,古道热肠的汽修厂老板张玉忠将开始参与交通事故道路救援,汽修厂将迎来搬迁,他将在户外遇到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2008年,他们将组建一支叫做“阳光”的救援队。他将为此失去一切,又拥有一切。
队长张玉忠。
(半岛全媒体记者 牛晓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