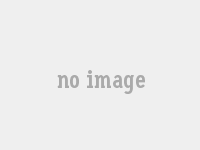“黑救护车”再次冲上热搜。
2025年7月1日晚,一名家属发文称,2020年,一名叫刘丽丽的女子因患风湿病到吉林大学第一医院住院治疗,医生未对她进行药物过敏、药物适应证和禁忌证方面的风险评估,给头孢类抗生素过敏的刘丽丽注射了头孢吡肟。两天后,医生告知刘丽丽母亲,刘丽丽需要到北京进行救治,随后刘丽丽被假冒“吉大一院”的救护车转往北京,途中,刘丽丽母亲发现救护车上的医生不是“吉大一院”的医生,车辆也不具备起码急救条件,连氧气瓶都不够用,且在服务区停车吃饭延误半小时,途中患者去世。
而在今年4月,江西唐先生的孩子患有重症,通过一家民营医院即南昌赣医医院的救护车从江西省儿童医院转运至上海一家医院,800公里的路程收费2.8万元,唐先生质疑其是“黑救护车”。6月18日,江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通报,证实南昌赣医医院存在收费不合理等问题。
不过,该通报发布后,一部分网友提出,800公里路途遥远,途中还使用了ECMO设备,2.8万元的收费并非完全不合理。尽管这一事件中的救护车是不是“黑救护车”仍存在争议,但更多人开始关注“黑救护车”。
“黑救护车”不是新现象。当前,120急救体系仅覆盖危急重症,这导致非急救转运需求转向民营机构,也就因此出现了缺乏资质、胡乱收费的“黑救护车”。
“黑救护车”为何屡禁难绝?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河南省平顶山市急救(指挥)中心原主任武秀昆长期关注“黑救护车”现象,他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出现“黑救护车”现象的原因错综复杂,主要原因是合理的医疗需求得不到满足,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建立统一的非急救医疗转运体系,让非急救医疗转运市场健康、科学、有序发展。
图/视觉中国
“‘黑救护车’小卡片装了好几个纸箱”
陈欣没想到,送病重外公从医院回家的短短3公里、10分钟路程,要花费1800元。
2024年8月,80多岁的外公已经在广东湛江一家医院住院将近两个月,患有心脏病、肿瘤等多种疾病,某天晚上突然全身冒汗,经抢救后身体仍持续恶化,直到几天后失去意识。“当时我们决定带他回家,于是联系科室主任,希望能安排救护车,对方说医院救护车不能送这种病人回家,但给了我们一个私人救护车的电话。”
陈欣对《中国新闻周刊》回忆,救护车一到,对方就开价2000元,“我舅舅和他说1000元行不行,对方说不行,最后谈到了1500元。回家之后,把我外公抬到屋里,对方拿出收款二维码,又提出要1800元,我舅舅没有心情和他争,就付了钱”。救护车上一共有三人,除了司机,一人穿白大褂,一人穿便服,“但是穿白大褂的人没有提供任何医护服务,只是坐在车上”。此外,救护车里只有一张移动床和氧气袋,没有其他医疗设备。
武秀昆曾围绕非急救医疗转运发表过几十篇文章,他总结,“黑救护车”有两大基本特征,即低成本投入和低成本运营。“黑救护车”的随车医疗设备通常因陋就简,甚至使用陈旧报废的设备以次充好,或者设备压根不能正常使用。另外,绝大多数“黑救护车”都没有医护人员随行,或者随车人员没有执业资质,“只是穿一件白大褂而已”。
正因为车上没有靠谱的随车医疗设备,“黑救护车”的危害也显而易见。《中国新闻周刊》查询裁判文书网发现,近几年,多地都出现了患者与医院和“黑救护车”之间的民事案件,涉及健康权、身体权、医疗损害责任纠纷,比如上文提及的刘丽丽案。
当前,“黑救护车”的现象仍然很普遍。一位应急医疗专家对《中国新闻周刊》说,2020年之前,他曾受国家相关部门委托,带队在全国10个省份开展“黑救护车”暗访,后因新冠疫情暴发而中断,最终暗访了7个省份、几十座地级市、上百家医院和急救中心,“省会城市全去了,每个省份至少去了4座城市,每座城市基本会去大学附属医院、人民医院、中心医院等”。
经过暗访,他们发现,大量医院门口都有“黑救护车”,医院的病房里,甚至医生和护士办公室里总能看到各种“黑救护车”的小卡片,“最后我们收集的各地‘黑救护车’小卡片装了好几个纸箱”。
广东民航医疗快线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民航医疗快线公司”)成立于2015年,是国内首家由省级政府卫生行政部门批准成立的非急救医疗转运机构,该公司董事长陈仲仁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十几年前,广州的“黑救护车”通常都由面包车改装,拉人就看“谁的拳头大”,乱象层出。现在,“黑救护车”大都有救护车的外观,挂着外地车牌,长期停在医院门口,甚至还有救护车冒充民航医疗快线公司,“打着我们的旗号,名片上印着我们的logo,写的是自己的私人电话,患者根本没办法识别”。
乱收费是“黑救护车”的一大特征。武秀昆说,这些车通常不会明码标价,并且往往低价揽活、中途加价,“举个例子,患者要从山西转到北京,正规的非急救转运公司可能要收5000元,‘黑救护车’会提出只收3000元,车开到一半突然提出加价到20000元,如果不给钱就必须下车,逼着患者及其家人给钱”。
“黑救护车”之所以总是坐地起价,与“黑救护车”团队的激励手段有关。武秀昆注意到,“黑救护车”通常有一个底价,即跑一趟能够回本的价钱,在此基础上,多出的费用有时会按比例给随车人员结算分成,“比如跑一趟3000元到6000元,可以提成10%,6000元到10000元可以提成20%”。正因如此,“黑救护车”的司机和随车人员具有很强的坐地起价动力。
“一个县一家,不为过吧?”
2023年,生活在天津的杨凌需要带母亲到医院看病,因为母亲的脊椎患有压缩性骨折,住宅楼没有电梯,所以需要有人抬着上下楼。杨凌认为,母亲在路上不需要医疗服务,没必要打120让急救中心派救护车,“感觉会浪费资源”,只想找能够接送患者往返医院的服务。
杨凌在社交平台上发帖分享了自己的经历,收到了大量评论和私信,来自各地的网友都表示自己有类似的需求,但是在当地找不到适合的提供医疗转运的机构。
武秀昆指出,“黑救护车”存在的主要原因就在于此——患者及其家庭对非急救医疗转运的合理需求得不到满足,至少在正规渠道得不到满足,供需矛盾和利益驱动结合,导致“黑救护车”屡禁不止。
什么是非急救医疗转运服务?武秀昆表示,这是“以救护车为主要交通工具和工作平台所开展的以患者转运为主的院外医疗服务”。具体来看,其服务对象包括例如自愿放弃治疗回家的患者、康复出院行动不便的患者、跨省转院的患者等。
而一个往往被忽略的事实是,公众对于非急救医疗转运服务的需求十分庞大。
太原市急救中心原副主任董钰柱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在太原,拨打急救电话的呼叫量中,高达80%是非急救需求,只有20%是真正的急救患者。而在北京,北京市红十字会救援服务中心副主任田振彪曾于2023年发表的《北京市开展非急救医疗服务的思考与建议》一文中指出,根据北京院前急救调查统计,目前拨打急救电话的呼叫量中有30%—40%属于非急救需求。
很长一段时间里,各地的急救中心承接了公众多元化的非急救医疗转运需求。直到2014年,《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办法》施行,其第二十七条明确规定:“急救中心(站)和急救网络医院不得将救护车用于非院前医疗急救服务。”
武秀昆参与起草了《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办法》,他说,之所以做出这样的规定,是因为各地急救中心经费由财政保障,很难实现既覆盖院前急救又覆盖非急救医疗转运。当个人因非急救需求呼叫“120”用车,会挤占有限的急救资源。
“急救中心的指挥调度,一般要求1分钟调度、3分钟出车、就近转送患者。如果急救中心各个分站的救护车大量被派去做非急救医疗转运,那么真正需要抢救的患者就可能得不到快速响应。”董钰柱说,禁止急救中心和急救网络医院将救护车用于非院前医疗急救服务,能够把有限的急救资源集中在真正的急救医疗工作上。
在《院前医疗急救管理办法》出台后,各地开始探索新的非急救医疗转运服务模式。地方探索中,一类是依托当地急救中心,在院前急救体系分出一部分力量,承担非急救医疗转运。此前上海和天津都是如此,即在120指挥调度中心设置了962120专线,受理非急救转运需求。
生活在天津的杨凌,就选择了拨打962120预约非急救转运服务。但是,多位接受采访的急救从业者对《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这一模式具有争议,因为许多急救中心的医生不愿意从事非急救转运服务,“非急救医疗转运通常不需要医疗服务,只需要搬运患者,医生和护士不想做这个业务”。另外,这一模式仍没有解决非急救医疗转运挤占急救资源的问题。
还有一类是依托市场,由政府有关部门牵头,引入企业参与非急救医疗转运服务。然而,各地的正规非急救医疗转运企业仍然相对稀少。
陈仲仁说,目前广州具有资质、规模较大、从事非急救医疗转运的企业只有两家。董钰柱表示,目前太原有三家正规的非急救医疗转运企业。武秀昆援引中国红十字会总会一项研究课题的数据,截至2023年6月30日,国内共有659家非急救医疗转运企业。“全国有将近3000个县级行政单位,一个县一家非急救医疗转运企业,应该不为过吧?但实际是没有的。”
正规非急救医疗转运企业的数量为什么远远满足不了实际需求?因为这并不是一门好做的“生意”。武秀昆说,相比低成本投入和低成本运营的“黑救护车”,正规的非急救医疗转运企业一旦运作起来,需要较高成本,赚钱并不容易。
山西陆航医疗国际救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西陆航”)成立于2019年,是一家经太原市卫生健康委批复的以医疗救援、非急救医疗转运为主营业务的民营企业。山西陆航总经理姜新良说,公司目前有33辆救护车,一辆普通救护车的成本至少25万元,车上还要携带便携式吸氧机、心率检测仪、吸痰器等设备,因此每辆救护车加设备的成本大约50万元。另外,姜新良表示,正规非急救医疗转运公司的救护车还要配备专业的医生和护士,具有较高的人员成本。
尽管非急救医疗转运企业的运作需要较高成本,但一到收费环节,企业和患者又存在较大的认知分歧。
近几年,杨凌多次使用非急救医疗转运服务,她认为非急救医疗转运的价格应该低于“120”呼叫的救护车。“我不需要太多急救措施,如果价格比120还贵,我用非急救医疗转运的意义在哪里?”而多位非急救医疗转运从业者表示,“120”呼叫的救护车由财政覆盖经费,具有公益性质、定价相对较低,企业却需要盈利,因此收费很难完全看齐急救中心的标准。
陈仲仁说,民航医疗快线公司的收费有最高限价,例如广州市内转运20公里以内的费用最高为600元,20公里至200公里以内费用最高为600元加上每公里30元,但实际业务中的收费不及最高限价的一半,“每公里12元都很难成交”。
由于“黑救护车”资金投入少,也就更有余力和正规的非急救医疗转运企业打“价格战”,把正规企业拖入无序的恶性竞争中。
中国国际救援中心西北应急救援总队总队长徐子钧说,2019年,中国国际救援中心组建了医疗救援总队,在甘肃开展生命救援转运服务。他发现,业务少的时候,“黑救护车”会把价格拼命往下压,正规公司很难竞争,而这里面藏着给患者挖的陷阱——“黑救护车”在拉客时,只会提到每公里路程的收费,等到人上车了,“各种花样就出来了”,开始询问是否需要氧气、是否需要呼吸机、是否需要医护人员,而这些服务都是另外收费的,并且没有透明的收费标准。
姜新良说,目前山西陆航在太原市内跑非急救医疗转运,基本是赔钱,只能靠长途转运甚至是国际转运盈利。
此外,一些地方“黑救护车”和医院之间的利益输送也在加剧乱象。董钰柱说,一些医院的保安队长自己就经营“黑救护车”,因为工作条件便利,可以只让自己经营的“黑救护车”开进医院,拒绝正规非急救医疗转运企业的救护车进入,“甚至有时医院的这个保安和这家‘黑救护车’有关系,另一个保安和那家‘黑救护车’有关系,两人为了抢生意还会大打出手”。
江苏淮安市一家医院外的私人救护车。(资料图片)图/IC
如何破题?
近几年,全国各地一直在加强打击“黑救护车”的力度。
2018年8月,国家卫生健康委联合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印发《关于贯彻落实〈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的意见》,明确提出要联合有关部门对“黑救护车”等现象进行严厉打击,净化行业环境。此后,多地开展了打击“黑救护车”的专项行动。例如2024年8月至12月,安徽省卫生健康委等4部门联合印发《安徽省开展非急救医疗转运专项整治实施方案》,在全省范围内整治“黑救护车”、规范非急救医疗转运发展。
不过,几位非急救医疗转运从业者都指出,这类专项整治往往只在一段时间内起作用,过一段时间“黑救护车”就会卷土重来。
武秀昆说,曾有地方官员对自己说,“黑救护车”的情况相关部门都知道,但是很难管。一个现实问题是,地方政府有时还存在一重隐秘的考量:在非急救医疗转运力量不足的地方,如果把“黑救护车”都消灭了,谁来解决患者合理的非急救医疗转运需求?
这也是为什么有不少网友批评江西唐先生的举报是“绝了别人的一条生路”。
因此,武秀昆认为,政府对于“黑救护车”的打击需要打组合拳,不仅仅需要开展专项行动,“关键是要解决合理需求”,也就是真正建立一个健康、有序的非急救医疗转运体系。他提出,现在各地对非急救医疗转运需求不同,工作能力基础也不同,全国层面的行业发展情况究竟如何仍未可知,需要先开展详细的摸底调研,在了解行业的真实情况之后才能开展清理整顿及后续工作。
目前,围绕非急救医疗转运,一些省市已经出台了相关政策文件,例如北京于2023年出台《北京市非急救医疗转运服务管理办法》,海南于2025年3月出台了《海南省非急救医疗转运服务管理办法(试行)》,但国家层面还没有全国统一标准。
武秀昆说,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应该“建章立制”,明确非急救医疗转运机构的职能和建设标准,并且“抓大放小”,适度提高成立非急救医疗转运企业的门槛。新申请成立的从事非急救医疗转运的单位可以按照标准对号入座,已经开展业务的单位应该对照标准限期整改,达标的续存,不达标的予以取缔。
正如“120”是全国统一的院前急救受理号码,武秀昆认为,还可以设置一个全国统一的非急救医疗转运受理号码,例如北京现在使用的“999”。
收费标准应该如何制定,是非急救医疗转运发展的另一重要命题。武秀昆认为,非急救医疗转运的收费应该先做成本核算,可以由政府部门出台有利产业发展的指导价,并由市场调节定价,“重点是必须要让企业盈利,否则没有人会来做这件事”。
现阶段,非急救医疗转运行业的发展仍需要政府给予适当扶持。武秀昆认为,财政可以适当投入,对非急救医疗企业进行资金补贴,“例如一家公司一年出车5000次以上,下一年每出一趟车补贴一定资金,补贴标准由政府公示”。
(文中陈欣、杨凌为化名)
发于2025.7.7总第1194期《中国新闻周刊》杂志
杂志标题:“黑救护车”现象调查
记者:张馨予 实习生:姚汶含
编辑:徐天